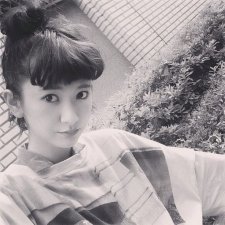爱你时光中凋零的颜(2)
他的生
叶芝和Maud Gonne第一次相遇时,他23,她22。都是彼此最美的年华。倘若二人同时坠入了爱河,这世上只会多一对才子佳人。可现实是,情感美文,叶芝深深地迷恋上了这个毅然放弃高贵的上流社会生活而投身于争取爱尔兰民族独立的运动的女子;这个女子身上坚韧不屈勇于抗争的光晕,挑动了叶芝懵懂的情思;他疯狂地爱上了这个“伫立窗畔,身旁盛开着一大团苹果花;她光彩夺目,仿佛自身就是洒满了阳光的花瓣”的女人,可是Maud却看不上这个彼时仍然心灵幼稚,生活贫困的穷书生。他默默地痴恋着她心中的女神,却不敢透露任何蛛丝马迹。高高在上的她,怎么会垂青于他这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呢?1891年,他以为Maud对他做出了爱情的暗示,于是兴冲冲地跑去求婚,自然被拒绝。这是改变他一生爱情命运的一件事。当火山喷涌而出,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它的蔓延了。他再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无法做一个安静的暗恋者。随后几年,他又对Maud进行了求婚,可是仍然被拒。Maud始终拒绝着这个深爱她的男人。即使在她与后来的丈夫离婚后,她也一直不肯接受这个已经将心捧在了她的脚下的男人。我们不知道原因,不能明白爱情的火花为什么不能发生在他们两个之间,只能遗憾和惋惜。不是每只蝴蝶都可以等到花开,不是每滴水珠都可以水滴石穿。
无望的爱成了叶芝写作的动力。诗人的不幸造就我们的大幸。其实早知道那些美丽的字句都是诗人作者的血泪铸成,为何后人还能有美的感动?“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千古一诗亦是一书生名落孙山后在极度失意中写就。“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在写了这首词后被一杯毒酒赐死。国家之大幸,诗人之不幸;诗人之不幸,文学之大幸。真是奇怪的因果循环。
爱的死
我总是会将这首诗与杜拉斯的《情人》联系在一起。文学上也经常将这两部作品比拟。虽然一个是诗歌,一个小说,但都共同倾诉了一个主题:时间与爱情。
“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情人》里那么多情绪,呓语,我却只记得这一句了,也是《情人》里最经典的一句。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能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初识时,你我是总角之交。我还有青涩的眼神,如云的青丝,你亦是鲜衣怒马,风流少年。十年后,爱恋荏苒了山河岁月,我的眼角却已爬上了蛇形皱纹,你亦不再是心思剔透,肯为我摘取山崖上的那一只玫瑰的竹马。时间把我们的爱情杀死了。前些日子我在微博上看到一张照片,两个老人头戴粉红色兔耳,深处闹市,笑的温柔自得。许多人将这张图片转发,想来如果是一对年轻情侣执手相牵闹市的照片,应该会是门可罗雀的转发量吧。
我们总爱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好像只要说说,就真的爱到老了。可是大多数说出这样山盟海誓的人不消几年便劳燕分飞了。新婚都没有,勿论金婚。
住在时光里的爱情,原来是经不住消磨的。
可是我们却仍然痴痴傻傻,有时候还怨恨为什么寻不到圆满的爱情。却不晓得从自身去找原因。当你能如叶芝那样爱一个人,不在乎是否有爱情的结果,不嫌弃爱情被时间摧残后的模样,你再去诅咒这个世界对你的不公平吧。更甚,爱情这朵花,还不是努力培育了就可以结果的。或许在你经历了千山万水的等待后,等待的也只是如叶芝一样的梦的破碎。
可是那种等待的幸福,不也是爱情的种类吗?
或许我爱你亲吻我指尖时新鲜的双唇 或许我爱你时光中凋零的容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