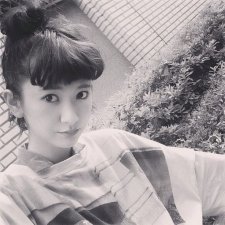愿我们一直心向阳光

时值深冬,阳光吝啬。不到六点,照耀天地间的一切光亮被集中回收,取而代之的是一幅漆黑的天幕,铺满整个天地。车窗外一切静寂,黑黢黢,吓人。近十点,乡间深冷的空气开始肆无忌惮地侵袭着我的躯体时,我们才到了目的地。紧紧了衣领,我快速走下车去。
突然一阵富有节奏感的鼓声、锣声间杂响起,让我精神一震,不由倾听。那鼓声雄浑有力,仿佛一把把小锤敲击在心脏上,一下一下。锣声清脆有质,恰似利箭之速迅疾地响彻耳边,一声,一声。鼓锣相合,或交替或混合,间歇发声,让我没来由地打了个寒噤,更加重了身上的严寒。
我知道,有人熬不住,在这森冷的冬日里逝去了,走向了一个不可知的世界。因为这鼓锣声,我熟悉得很,从小听到大。尤其是此地,留给我第一且最深的印象,就是这鼓锣声。从刚来后的每年冬季,孤寒里,声声阵阵,响彻不绝。那是亲人庄严的宣告,也是生命最后的叩问,更是灵魂最终的绝响。
我不知道,这乡间敲鼓打锣的风俗来源何时何地;我也不知道,在生命的最后历程里,奏响此声为何如此贴切;我更不知道为何每次听到此声,感觉总是渗人,鸡皮疙瘩起了一身。我唯一也许知道的是,它勾起了我的诸多回忆——那是我不到三十的光阴里,曾经亲身见证过的几次生命的离场,岁月的离殇。
1
我家大姑走得较早,不到三十五,生命之花就凋零了。记得那时我才读小学,一切懵懂之初,对生命没啥具体的概念。只记得有时听奶奶说,大姑她身体不好,经常弄药。我那时自认为她那几年身体素质差,时常患小感冒啥的,吃药就好。
结果年前的某一天,家里大人告知我,大姑走了,要我们去送送她。寒冬里,我们搭乘去县城的客车,两小时后才到了地儿。一下车,就是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起,然后阵阵鼓锣声传来。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鼓锣声,那时仿佛有一种莫名的悲伤在心底荡漾,不知为何。
不一会儿,我就见到了双眼红肿的堂妹念儿,还一直哭哭啼啼的。这可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小妹,那时关系可要好的。“哥,我妈不要我了,她走了,我一直喊她不醒。”念儿一见面就扑进我怀里,哭泣着说道。我也纳闷着,好久才从大人们叽叽喳喳的闲谈中知道,原来我的大姑真的走了,去了一个遥远的,没有劳累和疾病的地方,而且也永远不回来了。
大姑生来就勤劳,外嫁出去后也一直吃苦,那时在小城边做豆腐生意。每日拂晓,美丽心情,她就得起床,操持各种家务和磨豆腐等一系列繁杂工作,然后白日里推着车出去卖,一直忙到深夜。日复一复,年复一年,过度的劳累压垮了身体,挤压了闲暇,以至于身体有了小毛病也不加以重视。直到后来,她实在扛不住了,一检查才知道,胃癌晚期。
这下天塌地陷了,死亡的阴影随时笼罩着整个家庭,直到这一天的来临。下葬那天,我被早早地叫起床,忍着严寒,冒着寒风,给大姑送行。一里,十里,直到大姑家对面那个半山腰。我亲眼看见装着她的灵柩一步步被一锹锹泥土掩埋,然后覆盖。我终于失声痛哭起来。
我再也不能听见她,每次来我家时,老远喊我出来拿零食的声音;我再也不能听见她摸着我和堂妹的头,告诉我们兄妹要相亲相爱,互帮互助的话语;我再也不能听见,每次分别时,总是叮嘱我要好好学习,放假后有空到她家去玩的言语了。因为她静静地躺在那里,那个荒无人烟,杂草丛生之地,沉默无言。